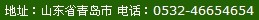|
公益中科 http://hunan.ifeng.com/a/20180327/6461888_0.shtml 我的故乡宿松,地处安徽最西南端,与江西九江的彭泽、湖口隔江相望,又与湖北黄冈的蕲春、黄梅毗邻。同时,宿松又处于大别山南麓,是长江流经安徽的入口处,被称为“八百里皖江首埠”。宿松境内,黄湖、泊湖、大官湖、龙感湖四大湖泊交叉相连,烟波浩渺,水质清澈,宜渔淡水资源极为丰富。辖区内“海门天柱”长江绝岛小孤山、保境安民的“南国小长城”白崖寨等驰名四方。从地理上说,宿松是楚头吴尾,宿松的山区、平原、湖区、丘陵,无不浸润着“物华天宝、人杰地灵”的吴楚文化风韵,同时又受越地文化影响。作为一座有着多年历史的古城,历代文人墨客如李白、王安石、苏轼等曾游历宿松且留有诗文。在《赠闾丘宿松》一诗中,李白写道:“夫子理宿松,浮云知古城。”在宿松县城南1.5公里处的南台山,至今留有“太白书台”的遗迹。 年,我从乡下到县城里的宿松中学读高中,从此开启了在这座古老县城里的一段生活。父亲那时候在县教育局工作,单位有一间平房作为宿舍,所以我没有像其他乡村来的同学那样住集体宿舍,而是和父亲住在一起。每天早晨,我背着沉甸甸的书包,先是步行走过县实验小学浓荫蔽日的梧桐小道,跨过窄窄的青石铺就的南门街,然后穿过老邮局旁曲里拐弯的小胡同,再经过一片弥漫着油条、包子、馄饨、烧卖气味的早餐市场,走过一片不时坐着三五钓叟的黎河塘,最后经过一个酒糟味十足的酒厂,大约半小时后,才走进宿松中学的大门。 学习时间之外,我会在城里闲逛。县城不大,也没有什么高楼大厦,有的只是老街、老巷、老屋,如方家弄的黄家大屋,高家弄的高家祠堂,南门街的徐家祠堂,等等。爱好文学的我喜欢这些略带沧桑的地方,古城老街在我眼前呈现的不是破败,而是古朴幽静的诗意。街巷路旁,随处可见香樟树、桂花树,皖南地域丰饶的花花草草,与古城独特的烟火人间,弥合成一种令我迷恋不已的气息。这里有新华书店,还随处可见书报摊,可以买到心仪的文学期刊。这里还有电影院,有黄梅戏剧团,有灯光球场,有热闹的人民路……那时候,我常常想,我以后就要在这座城市里工作和生活! 年的秋天,我离开了故乡宿松去上大学。此后越走越远,最终在遥远的北京定居,忘却了当年要回到县城工作和生活的梦想了。虽然每年都有机会回到宿松看望父母,但只是短暂的逗留。 30多年的时间似乎是一晃而过。不经意间,出走宿松的少年已到了中年。年,留在县城工作的同学组织了一场高中毕业30年的聚会。同学相见,分外亲切,时光在每个人的身上都留下了痕迹,老师们更已是“鬓已星星也”。我们在新建成的宿松中学食堂,不约而同地怀念起那踩起来咯吱作响的宿中旧木楼,怀念起那如四合院般的平房教室,大有恍如隔世之感。 这几年,我与宿松又有了很多次“亲密接触”。我的老母亲年近九旬,不习惯北京的生活,甚至不习惯县城的生活,大部分时间就住在离县城不算很远的乡下老宅。因为挂念母亲,我每年都会想方设法回几次宿松,在老家住上一段时间。我发现,故乡不知不觉有了“纵使相逢应不识”的巨大变化,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县城的格局和面貌上。上世纪80年代我们眼里宽阔无比的人民路,早已被一幢幢现代化的楼房包围了。县城里新建成了四通八达、纵横交错的陌生大道,道旁高楼鳞次栉比。有的街区旁边,就是美丽的公园。公园背靠山地,里面遍布绿植与鲜花,间杂湿地与沟渠。让人觉得,城市与自然已经完美地融为一体。我想,这哪是我记忆中的故乡啊,变化真是太大了! 故乡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让我高兴。尤其令我高兴的是,高铁宿松东站于去年正式开通运营,这意味着我从北京往返宿松再也不用火车转汽车,省却了很多旅途上的麻烦。巧的是,宿松高铁站离我老家村庄不远,不到3公里。今年暑假,我第一次坐上了连接北京与宿松的高铁。我注意到,宿松高铁站的外观设计很像一个黄梅戏戏台,这个灵感和设计理念大概与宿松人爱唱爱听黄梅戏有关,也许还有文化搭台、经济唱戏、发展宿松的美好寓意。最近又看到来自老家的消息,随着城镇化发展,与我家毗邻的“五里乡”改成“松兹街道”了。这意味着,与我的村庄一河之隔的邻村已经变成城区了,而我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也自然成为城郊了。 返京前的一个清早,我和一位老同学在池塘边垂钓。当我们坐在小马扎上静候鱼儿上钩的时候,晨光熹微,微风吹拂下的水面呈现一圈圈的涟漪,透出十足的诗意。我忽然想起唐代诗人司空曙的《江村即事》:“钓罢归来不系船,江村月落正堪眠。纵然一夜风吹去,只在芦花浅水边。”我衷心希望,故乡宿松越变越美好,越来越发达。同时,又能守护好那些最美好的东西,让一代一代的宿松人始终能够“望得见山,看得见水,记得住乡愁”。 《人民日报》(年11月23日15版)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:http://www.13801256026.com/pgzp/pgzp/8039.html |
当前位置: 宿松县 >浮云知古城我与一座城
时间:2024/11/1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上一篇文章: 新春走基层安徽宿松现代农业园里的好年景
- 下一篇文章: 宿松积极推进困难职工帮扶工作人民资讯